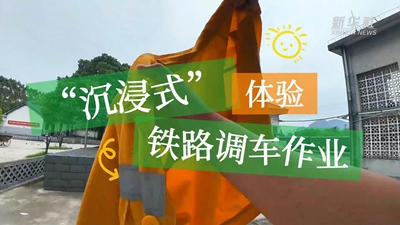大风过后,灿烂的阳光照耀在格尔木河上,来自昆仑山的雪水告别一冬的寒凉蜿蜒成一条银链,被滋养的城市村庄也变得闪亮清澈。河岸边的青杨正在褪去羞怯,枝叶冒出绿芽,斑驳的树影斜斜地漫过河滩上矮矮的红柳丛。
家住青海省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众祥村社区的护林员严兴花踩着松软的沙土巡护,红色头巾在一片嫩绿中穿梭,她抬头迎接穿透云影移动的光线,眼里眉间多了几分舒展:“离家只有两三公里,几乎每天都来,风来了关注火险,雨来了观察水量,日志上写清楚树木花草的四季变化,心里有劲,总想着日子还能更好。”
可十几年前,严兴花却很难有这般心情。公婆常年患有慢性病,丈夫心脏不好干不了重活,还要照顾两个上学的孩子没法出门打工。家里做饭、洗衣、照顾病人,地里耕种、施肥、浇水,都指望她一个人。“春天是难熬的季节”,她印象中的格尔木“树少,还瘦,一进三月就是数不尽的风沙,连碗里的水放半晌都能搅成泥浆,眼前灰灰的,心里也是。”
河水在昆仑峡谷中劈开绝壁对峙,不断流淌,如今下游城市推窗见绿,行路见荫,戈壁滩被绣上了青翠的补丁。从沙到绿似乎仅一步之遥,但只有河水和亲历者才懂得,数十年如一日灌溉滋养,唯心诚才实现跨越。种树,养树、护树,老一辈用肩膀挑水、用脊梁挡风到后代们挥汗挖渠,引水涵养,70、80后一代代精心巡护,持续植绿扩绿,连片的绿洲缚住沙尘,数百户严兴花们以“护林员”为傲,每月拿3700元工资,过上了有盼头的日子。
拥抱河水的馈赠,初代移民几乎都有类似的集体记忆。在众祥村社区书记窦万娟眼里,“格尔木”这个蒙古语被译为“河流密集的地方”名副其实,她家祖籍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县大河家镇,20世纪80年代,因地少、干旱,为养活全家,父亲远走格尔木当“淘金客”。“金子没找到,找到了大片的河滩滩,挖坑三四米就有水渗出来”,随后,一家人跟着父亲搬了来。七八岁的孩子们都听大人们说,山上的雪水营养丰富,虽然荒地盐碱度高,但只要“把水用起来,把地开出来,肯定不能饿肚子”。
挨饿,很多中年人已经没有这样的记忆,但窦万娟有。“家里兄弟姊妹4个孩子,我是老大。弟弟老提起,说我有次干完活回来,饭吃了十几碗。那也只是飘了几块面片和洋芋的清汤汤呀,十来岁的年纪,每天只觉得饿。”浓眉大眼,说话利索,衣着得体,42岁的窦万娟全身都带着一股能干事、干成事的劲儿,“都是生活磨出来的”。母亲去世早,知道考了大学家里也供不起,她上完高三第一个学期就跟同村的伙伴们扒火车去兰州进货,到市场摆地摊,“还在瓜摊下面捡过西瓜皮,洗干净炒菜吃”。
从家家门口打“压水井”到修土渠引河水浇地,再到用水泥板铺设明渠,又到现在的混凝土浇筑暗渠,河岸荒地越种越肥,水脉上长起了新城。窦万娟所在的村子由几十户增加到上万户,最初叫“东村”,后来划分成6个村社区,“位于市郊,还有农田,所以叫‘村社区’,众祥规模最大”,2200多户1.1万人,有汉、回、藏、东乡、撒拉等民族。往上追溯两代,大多是从缺水山区来的移民,人们因水而聚,百业随水而兴。
在荒芜中坚持热爱的勇气,逆境反而成全。窦万娟开起品牌服装店,嫁在本村,生了儿子,和父亲一起供弟妹们上大学,还承包了30亩土地种枸杞。“一辈子没走出去”,她话里说着遗憾,语气却踏实而满足。连村里的老人们都常说,没料到,当年只能种一点小麦和洋芋,如今,连片的枸杞林,种出西红柿、黄瓜等等蔬菜的设施大棚,多种景观绿植分布的河边湿地公园……大地和河水给勤劳的格尔木人送来礼物,早年移民这里,来对了!
跟着晒太阳散步的人们沿河岸往西走,碎片化叙事中那些被晒爆皮的脸颊、被风沙侵蚀的农田、被大风掀飞的屋顶,都已经留在时间的裂缝里。城市另一侧,察尔汗盐湖卤水池倒映蓝天,机械臂在盐田上划出几何纹路。钾肥与锂盐从这里流向全国,支撑起中国盐湖产业的脊梁。工人们说,盐湖结晶里藏着河水的密码:“没有格尔木河补给地下水,哪来这数十亿吨的‘白色宝藏’?”
夕阳西沉,格尔木市东出口光伏产业园的4400面定日镜集体转向,将落日的光折射成璀璨星河。塔式光热电站的吸热塔宛如现代版昆仑神柱,年发电量1.2亿千瓦时的数字背后,是格尔木河哺育的另一种能量——清洁能源装机量突破1000万千瓦,光伏板阵列从河畔一直铺向天际,恍若一片停泊在戈壁的蓝色海洋。千亩林管护站,一名工作人员轻轻叩响沙枣树干,惊起几只红嘴山鸦。树影婆娑间,她重复老站长的话:“种树不是和老天爷较劲,是教沙漠学会记住绿色。”
高原上一张张迎接春天的面孔灿烂又温暖。暮色中的格尔木河奔流不息,第一轮春灌已经结束,抢抓春时的人们脚步轻快,而围绕河水展开的故事,仍在不停书写……(记者王大千 陈杰)